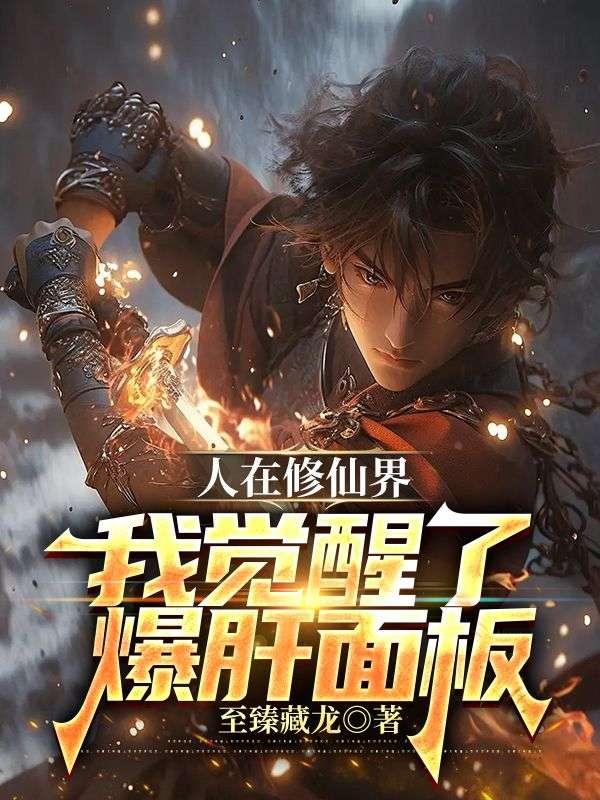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双生夫郎互换人生后TXT > 第214章 乌平之洪楚2(第2页)
第214章 乌平之洪楚2(第2页)
他又想,结连理做什么?
事有好坏。这件事的好处在于,他可以跟洪楚同进同出,同食同寝。坏处是,洪楚会多一层来自世俗的束缚。
若是束缚,那就不要了。能这样也很好。
他一直藏得很好,直到去年查考绩,被洪楚察觉了异样。
百姓有副业,算不上经商,税收不变;百姓富裕了些,县里没有巧立名目加征,收税总额未有提升。
但县里办了件好事。经过三年的努力,沟渠挖通了,水车建设了,他们引水到田,这是利于农事,利于民生的大好事。他还有一街街、一村村走访的“苦劳”。一片为民之心,日月可鉴。
这个政绩,好也行,差一点也可。他这样机敏,善于交际的人,偏偏没去打点,还真就差了一点。
洪楚过了好几天,来找他放了话。他答应成亲。
乌平之没有丝毫惊喜,只感觉从头到脚被人浇透了冰水。他浑身发抖,脑子发木,嘴皮子都不利落了,上下相碰,只会说“不要”。
洪楚耐着性子,跟他说了两句场面话。
什么他们年岁相当,性情相投,又什么他不想再等了。软话说了,乌平之不松口,洪楚便转换了态度,只剩强硬:“我等你来提亲,不来就不用再见我了。”
他放了话,也不与乌平之磨嘴皮子,转身就走。
乌平之追着他拉了数次,都被洪楚甩开。眼看着洪楚要踏出门外,他只好动作粗鲁的把人拽回来,不管他的挣扎,把他堵在了门后。
乌平之语气近乎低吼,“这件事是我没有办好,但我绝没有以此逼你的意思!你要这样想,那你就是小瞧了我,也作践了自己。我不忍看你因为无奈、因逼迫,因与你无关的情意而妥协。就算那个人是我也不可以。”
洪楚没吭声。乌平之常看他像一朵蓝色焰火,但他的外貌气质都很冷俏。他们初次见面时,他看洪楚像腊梅。现在更甚。
乌平之说:“我知道你的才干、你的抱负,我知道你走到今天有多难,我更知道你领着族人另起门户的担子有多重——”
他忍不住伸手,却不敢碰洪楚的脸,手心几乎要碰到洪楚脸上的绒毛,呼吸都能感受到热度,眼里只有彼此的样子。
他说:“你听着,我的确想要你心甘情愿的接受我,和我成亲,但我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,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和世上其他人一样欺你逼你,拿情拿义相要挟,让你被迫说愿意。我绝无这样的想法,我敢想敢做就不得好死!”
洪楚眼里有泪光。离得太近了,任何神态都无处掩藏。
那只与他脸颊保持着些微距离的大手,终于有了落下的理由,掌心贴着他的脸颊,指腹给他擦去了泪痕。
他又偏偏不是软弱性子,只这一瞬,他就推开了乌平之,恢复了平常模样。
他说:“那好,我收回我的话。”
洪楚再抬手,把乌平之抓着他手腕的手指一根根掰开。
“以此为期,一年之后,你来找我,我会给你答复。”
-
一年之期到了,乌平之问了,洪楚答了。很平常的一天,却酝酿了一年。洪楚还对考绩之事耿耿于怀,总觉亏欠。而乌平之不觉可惜。
他到家,使唤小厮们去唤人,把族人叫来,通知了一件事。
“我要成亲了,会备聘礼,择个良辰吉日去下聘。”
下聘,一听就不是嫁人。
屋里的洪家人都很震惊,互相看一看,七嘴八舌的忙起来,劝他别冲动,说婚事不同儿戏,要谨而慎之。
还小心试探他跟乌平之的近况,是否吵架,又或是乌平之等不了,要说亲了?
洪楚听到这个,才发现在旁人眼里,他跟乌平之的关系有多不正当。
他挑挑眉,逗话道:“对,乌大人也要成亲了。”
这个结果让人意外,又非常合理,他们愤愤不平,却能理解。乌平之今年二十六还是二十七了?拖不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