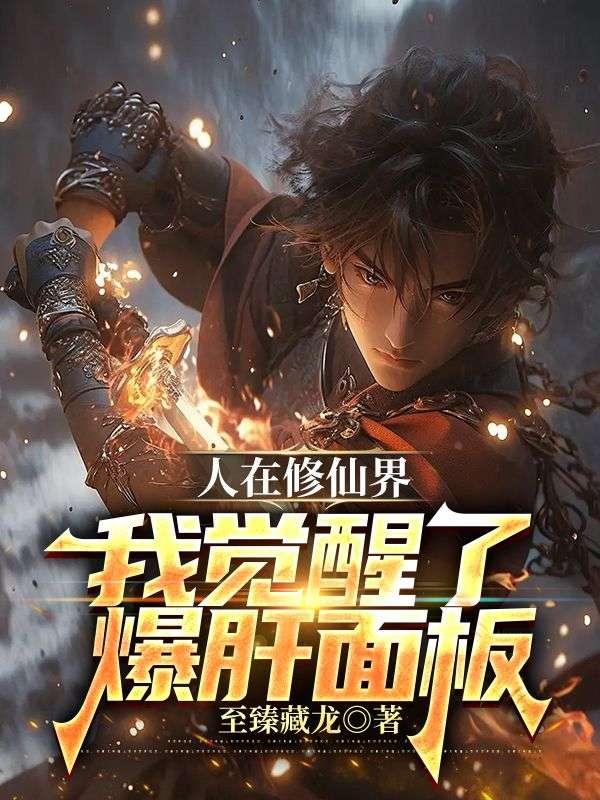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虫族之强制匹配玄朱 > 第035章 西恩的回忆下(第6页)
第035章 西恩的回忆下(第6页)
圣廷那边,贝卓死了。教宗病了。就连一直争权夺利的理查德都死在了前线。
身边的虫一只一只死去。
萨洛提斯公爵、林德元帅、教宗、陛下……
之后,圣廷和帝国覆灭,新政府建立。
我和阿尔托利共同经历了许多事,我们关系日渐亲密,成为了彼此没有血缘的家人。
这十几年,我眼睁睁地看着,阿尔托利从意气风发、恣意张扬的少年雄子,被生活世事磨去了尖牙利齿,变得圆滑妥协、温和被动。
有时我在想,这还是我爱上的那只雄子吗?
太多不动声色的隐忍、太多疲惫不堪的眼神、太多故作的温柔和善,就像将他装进了一个同名同姓的精美皮囊,乍看还是他,再看,又觉得哪哪都不像。
可又清楚地知道,他是一步一步,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。
从十六年前起。
从我大意让出了他身边那个位置起。
从他用圣言之力救了我开始。
从命运对他张开獠牙、而他毫无准备时。
每每夜半惊醒,总是在黑暗中痛恨自己,设想无数个如果。
其中最重要一条,便是要教他有防人之心,教他信任脆弱且不可得,教他如何辨别野心和贪婪,教他明了自己是什么身份,在什么地位,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。
又觉不忍。
想必当年的虫帝陛下和教宗阁下,和我此刻是同样的感受。
如此柔美漂亮的玫瑰,如果拿去透明的玻璃罩,在狂风暴雨中还能存活吗?
怕不是早就枯萎败谢,沦为一地齑粉。
其实他比我们想得要坚韧许多。
曾经一言不合就会暴怒的少年,学会了推杯换盏间谈笑风声,与狡猾如狐的官员斡旋谈判。
我的许多旧部便是被他这样一只只,拉出泥泞沼泽,逐渐在新政府有了立足之地。
他还为我找了一处极好的去处。
战前革命军中最让我头疼的难缠敌手、却也是相惺相惜的对手所指挥的军团。
我被编入他的麾下,得到了远比职务更多的统辖权和尊重。
我可以尽情地在前线厮杀,发泄我的愤怒和暴虐,而不用被当做工具争权夺利、最后顶着一身脏水,连个埋尸地都无。
他可能不知道,但事实上,我极为依赖他。
很多帝国的旧臣和议员,也开始依赖他。
我们这些停留在过去不肯向前的虫,悄无声息地结成了一个同盟,在新政府各党派的血雨腥风斗争中,等待着那个合适的机会。
与此同时,我在全星际寻找虫族曾居住过的母星。
越久远越好,越古老越好。
还有各个星球上的大大小小的圣廷遗址。
阿尔托利曾有过一枚上古之戒,名叫海勒斯。
戒指的材料和镶嵌的宝石,都是来自这些曾有虫居住,但现已被遗弃的母星。
克墨斯是里面唯一延续至今,还有虫居住、且繁荣至今的星球。
在我最颓废的那段日子里,我曾把圣廷典籍当睡前故事读,用来催眠。
那东西阿尔托利的公寓里有一堆。
里面有不少传说故事,而很多故事,都提到了“异宝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