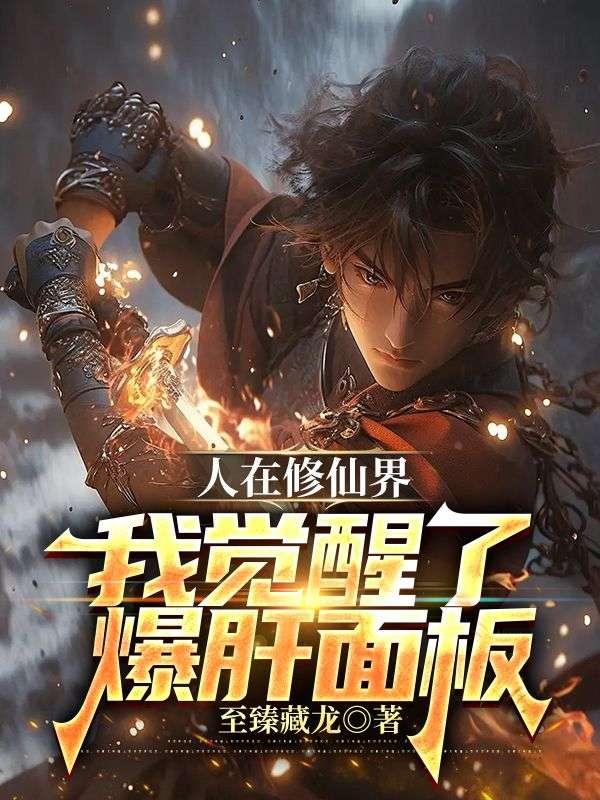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啊?这里是规则怪谈?移鼠怪谈TXT > 第47章 两个方向二合一(第4页)
第47章 两个方向二合一(第4页)
可那个扭曲的榕树怪谈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形式为他触发,没有实现他的愿望,以一种极度令人绝望的冷漠,把他依然钉在这里,钉在一个常人的形态。
所以,现在,他要离开这片没有湖水也没有暴风雨的世界,去往那个八年前榕树最为繁盛的时刻。
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自己被困在水中漂浮物上的样子,他提着不知道哪里来的矿灯,哼着屏屏喜欢的儿歌,不紧不慢过来,歌声十分放松,腔调字正腔圆。
另一个画面,是他冷冷地告诫我,让我不要跟着淌这趟浑水,却没有给我做过多的保护措施,好像早就知道我不会真的出事,能够逃过万一可能的“坏结局”一样。
再一个画面,是他在那些浮水尸里,一个一个辨认过把人救上来,没有丝毫不耐烦。
直到他敲开青石,也许那一刻就直面了镶嵌在石壁上的妇人启门图,平静地把里面的人也挨个拖出来。
这一次,不同于湖水中被他救上去直接丢给我的那批伙计。
他是很详细地把处于榕树和青石争夺之间的人,好好端详了一下,确认对方的五官面容。
隔着那个深潜的距离,也许我错过了他一瞬间的失望和释然。
再后来进入青石不见踪影,他也许是想把还困着的高六救出来的,但他最终的目标依然只有一个。
所以回到现在,他一直看着我不停地疑问并推论,有时候哪怕是在做无用功,也没有阻拦或者帮助我。
他是在等着。
等着我先从周听卯的最后馈赠那里得到足够的洗礼和屏障,等着让我自己形成足够明确坚固的恐惧和愿望。
我竟然没有想过,在两个世界线的跳跃上,我们的最终方向是相反的。
我是从那个坏结局逃逸出来,他却是要一头撞回去。这个也许是好结局的世界对他来说竟然无可留恋。
一股莫名的悲凉涌上心头,我大概是心里非常痛苦骂了一句神经病,人非草木,不怕我现在改了执念吗这个疯子。
还没有来得及细想,小队长张甲忽然道:
“看屋顶。屋顶那里是不是有个尸体露出了一些边角。”
“不,不对,那人是不是套着个下水的装备还是什么啊?”张甲看了看,问身边其他伙计,“都是爬山虎看不清,谁认一认?”
我脑子里嗡了一下,明知道不会是张添一,但还是引发了某种近乎心理阴影的退缩和排斥。
“——少爷?”张甲看看我,他不知道刚才几句话的功夫,随着张添一的离开我这里经历了多少波澜,有些担忧。
“怎么脸发白?你要再歇会儿吗?”
我悚然回过神。
不能变,这就是我要做好的事情,像眼镜儿交代的,我得一直往前面走。现在,其他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他们闭环内的事情了。
“……走。”我大概是咽了口唾沫,感到一旦迟疑,事情的整个局面就会往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个方向转变。
我用了三分钟检查自己的体力和注意力,让张甲帮我把身上的装备也再确认一遍不会临时出什么纰漏,用力搓了一下手,把手搓热,接着开始拍打自己因为紧张而绷得发僵的面颊。
由外向内看去,那一片清凉的绿荫无比真实,但全部是榕树。
两边,各自八棵榕树,对称地并列排开。地面的土壤翻起,凸出的全是杂乱如同蟒蛇一样的树根。
但这些榕树也是死的,上面的绿色全是绢布,绒面的叶子栩栩如生,就像是永远凝固了一样。
中间的鹅卵石小路一路延伸到红砖墙和一扇半开着的铁门前,往上看,趴在墙上的爬山虎纹丝不动。
不,不是爬山虎,那也是榕树。
那是爬满了墙面的无比细小的气生根,因为枯萎后已经近乎于藤蔓的细细卷须一样。上面覆盖的也不是倒卵圆形的爬山虎叶子,同样是一片一片绢布裁剪出来,逼真到极点的榕树叶子。
整个民宿从前方空地开始,就像一整个精致而毫无生命力的巨大玩具。
“现在我们就进去,看看最后一块拼图是什么。”我说,踩上了鹅卵石小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