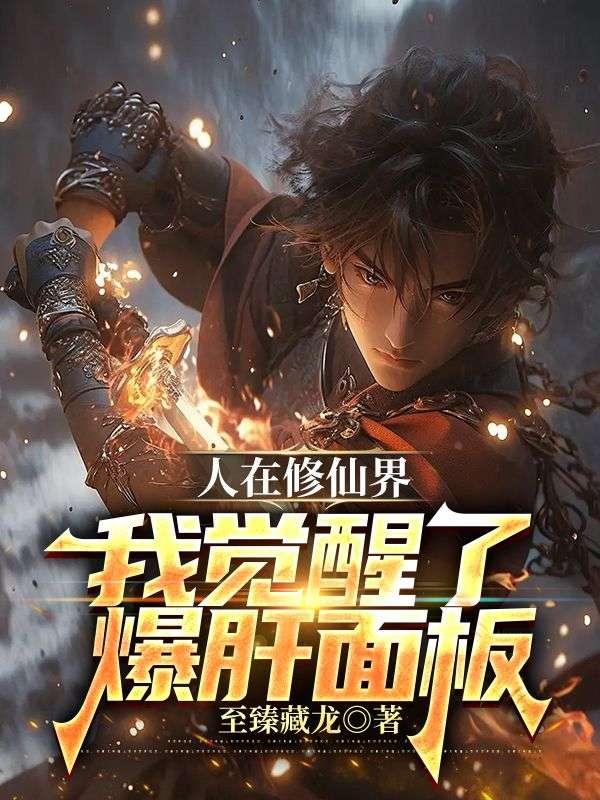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啊这里是规则怪谈by来点薯条 > 第70章 区分(第3页)
第70章 区分(第3页)
以至于我迟钝想起车上被剐蹭过时,还十分自然地认为这就是唯一的伤势,觉得他们不知道我“受伤”是正常的。
我靠,这是怎么发生的,为什么一点迹象都没有。
我在看张添一眼中的疲惫,简直过电一样。
心中有个声音大喊,对啊,人本来就会疲惫、会受伤、会死。我在酒吧里,念头是怎么一步步偏转,毫无问题就开始认同“虚弱和受伤才是不正常”这种结论的?
他和掮客,还能保持正常人的状态,顶多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被移鼠污染。
而不是忽然滑坡到他们不符合移鼠的规则就不算人。
可怕的是,在离开酒吧之间,我一刻都没有感觉到这个逻辑逐步滑坡的荒谬。
也就是这一刻,那些被我遗忘的疼痛一下子火辣辣全部烧了起来。
“座位下面,消毒的都有,自己拿。”
张添一看着前方说,好像真就专注于蹬车一件事。
我浑身冒汗把座椅掀开,取出里面的小医疗箱,咬牙给自己消毒处理伤口。
由于那些树根半天没人处理,几乎全部钻到了镊子够不着的地方,我不得不从张添一那里抢了把锋利的匕首,消毒、点火,在火上撩了消毒后把微微结痂的伤口重新割开扩大。
这个过程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,只处理了一条胳膊,我就浑身哆嗦得几乎要虚脱了。
“医疗箱最底下有啤酒。”
张添一又道,“吃烧烤的时候顺的。然仔,自己行不行啊?”
我怒视让他滚蛋,咬牙拧开医疗箱,给自己硬灌了两口啤酒,差劲的酒量让我原本应该已经发白到没法看的脸轰一下红了。
有点熏熏然的醉意让痛感降低了一些,但还是很难忍受。我足足缓了十分钟,三轮车已经离月台小楼极近,我才擦着止不住的冷汗对自己继续下狠手。
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认知偏差太让人发毛了,我也不想浪费现在痛彻心扉的酸爽感,就靠着刺痛开始梳理:
“一开始,只是了解移鼠为我们、为人制定的规则……但讨论久了,就潜移默化,变成了我们公认的正常现象?移鼠对人的定义,是不是在逐渐取代掉人本来的定义?”
像雷子哥或者现在的我,因为身体上的伤无法忽视,一直断断续续对自己的潜意识有着提醒,还能时不时产生“受伤”这个概念,感到疑惑。
但其他人呢?看样子连女队医后来都忘了拿出来的医疗箱是为我准备的。
所有人就这么堂而皇之放任我一个刚救出来的伤者在聊天谈论,丝毫不怕我随时被树根寄生过重猝死。
我是越想越不对劲。
一方面,这让我意识到,掮客之所以能够保持清明,是不是身上也有很重且持续的伤口,重到无法忽视,才能做到不失清明。
另一方面,她选择毫不犹豫让我走,而不是提醒徐佑这个曾经的伴侣。
是徐佑他们现在的认知偏差过于根深蒂固,暂时无法被纠正,纠正后很快又会遗忘吗?
“不行,我们真不把师母带上吗?”我有些隐约的不安,“放她一个人在房间,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变故?”
“没事。”
张添一难得踩停了破三轮,转头来看着我的眼睛,轻声道:
“他们进不去休息室,碰不到她。”
什么意思。我的冷汗一下就下来了。
“字面意思。”张添一笑了笑,有些感慨,“你提醒得对,我也差点又要忘记了,忘记自己为什么去大张旗鼓的做那些事。”
“然然,及时回头来找你求助是对的。”
——哪些事?
被揭开这层要命的迷雾后,我的思绪变得清晰无比,再没有那种认识偏差后间歇性的懵懂恍惚,立刻想到了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