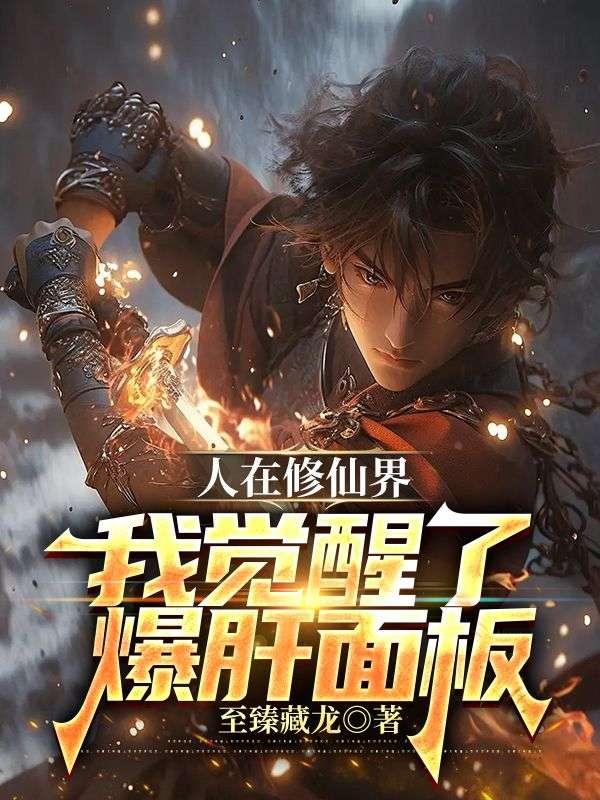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忍界从木叶开始的虫姬 > 第5章 渴望新鲜血液(第1页)
第5章 渴望新鲜血液(第1页)
空调冷凝管在窗外规律地滴水。
苏瑾缓缓地睁开眼,天花板的霉斑像具吊死的尸体。
他保持着蜷缩的睡姿,鼻腔里充斥着熟稔的酸腐味——既不是厕所地漏反涌的沼气,也不同于厨房角落的烂菜叶,更像是生蛆的猪肉在塑料膜里发酵的味道。
母亲的工作靴整齐地摆在玄关,鞋底沾着化工厂特有的淡黄色粉末。
餐桌玻璃板下压着褪色的全家福,父亲的面容已被阳光晒成了灰白色。
苏瑾睡醒后踩过开裂的瓷砖,地板缝隙里还粘着去年除夕的爆竹碎屑。
卫生间镜面蒙着水雾,他在上面画了个绞刑架。
发黄的美工刀躺在洗手台边缘,刀刃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渍——上周他用这个削苹果时划伤了手。
当冷水扑在脸上时,喉结下方的两个暗红牙印隐隐发烫。
厨房飘来隔夜咖喱的哈喇味,冰箱压缩机发出哮喘病人般的喘息。
苏瑾从橱柜深处翻出袋装方便面,指尖触碰到某个冰凉坚硬的物体。
是那把用报纸包裹的剁骨刀,刃口沾着褐色污渍。
他顿了顿,将刀推回阴影深处。
管道井突然传来重物拖拽声。
苏瑾贴着斑驳的墙壁挪到门后。
猫眼像颗混浊的眼球。
对门铁门发出锈蚀的呻吟,一个谢顶男人臃肿的后背堵满视野。
深蓝色垃圾袋被拖动时隆起不规则的形状,男人抬脚将凸起踩瘪,使塑料袋发出黏腻的挤压声。
腐臭味骤然浓烈,像有人把死老鼠塞进了鼻腔。
苏瑾的太阳穴突突跳动,喉结下方的牙印变成灼热的烙铁。
当男人第三次折返搬运时,运动鞋底拖出的暗红痕迹在水泥地面延伸,如同蜗牛爬过的黏液。
苏瑾退回卧室,从床垫夹层摸出偷来的预付费手机。
“说。”叶栾雨的嗓音裹着电流声传来。
“邻居在运尸体。”苏瑾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。
对面传来纸张翻动的轻响:“细节?”
“右下方有红色三角形回收标志,捆扎手法是活结套死结。”苏瑾注视着第三个垃圾袋滑进电梯,男人油亮的后颈泛着尸斑般的青灰,“袋口渗出的液体在水泥地凝结成胶状物。"
通话陷入短暂静默,远处化工厂的排气阀正在释放蒸汽,白雾顺着锈蚀的管道爬升。
叶栾雨的呼吸声在电流干扰中变得绵长:“有进步。”叶栾雨夸赞道,“上次来你家做客就发现了——那股尸臭都渗进墙皮了。”
苏瑾的指甲在窗台划出刻痕。
那些被当作管道反味的日夜闪过眼前——母亲抱怨对门垃圾处理不当的每个清晨,自己擦拭通风口霉菌的每个周末——此刻铁锈味的空气突然变得粘稠,像灌进肺里的血沫。
“现在我闻得出来。”
他通过猫眼盯着男人领口的褐色污渍,“就像能看见你牙齿上的血。”
“毕竟经历过了。”叶栾雨再度赞许,“又问,“你闻到茉莉味了吗?”
苏瑾的鼻腔黏膜刺痛起来。
腐臭味中确实漂浮着一缕甜腻花香,就像殡仪馆用来掩盖尸臭的廉价香精。
被汗浸湿的手机外壳在掌心打滑,他在裤缝上蹭了蹭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