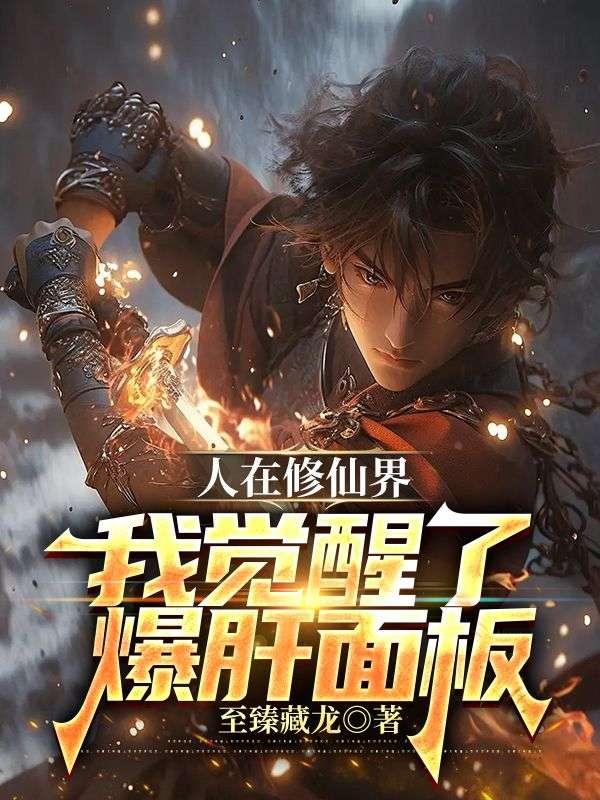笔看阁>穿成镶边女配的她们最新章节 > 完结(第7页)
完结(第7页)
商枝碾碎了脚下的一截枯枝,抬脚走了进去,踏着一地辉煌烛光,站在两排煌煌烛火中间,鸦羽似的漆黑眼睫撩起来,仰头望着高台上的石像。
这石像焕然一新了,那些细小的蛛网和灰尘全都不见了,持剑的剑客眼眸微阖,唇角浅笑,她的眼窝被烛光点亮了,一汪金色的光汇聚在里面,身后背着的净瓶插着翠绿的柳枝。
商枝看着这石像,忽然觉出一丝熟悉来,好像有那么一年,她因为鬼阵反噬高烧不退,被老疯子扛到一个破庙里,半夜烧的迷糊,老疯子就折了夜里带着露水的柳枝来来回回扫着她的脸。
柳枝上的露水冰凉冰凉,那个庙的瓦片破了一个大洞,睁开眼,能看到好多好多的星星。
她迷迷糊糊地起来,觉得自己小命不保,又觉得老疯子这人疯疯癫癫,实在不靠谱,就拿着罗盘去外面给自己选埋骨用的风水宝地。
刚找到一块地,正准备挖个坑躺进去,老疯子骂骂咧咧地把她扯回来,她抓着旁边的老滕树不放,拽下了一手的鹅黄色小花。
老疯子把她拽回破庙里,她像头倔驴似的又跑又跳,也不知哪来一股牛劲,硬是爬到破庙里的石像身上,把手里拽下的鹅黄色野花揪下来,簪在了石像的眼眶里。
幼年的商枝胡闹了一通,病得更严重了,后半夜睡不着觉,总觉得鬼影在眼前闪来闪去,老疯子给她喂下了安神的药丸也不好使,直勾勾地睁着眼睛不肯睡觉。
老疯子没办法,只能摇晃着手里的金柳枝,现编了一首童谣哄她。
老疯子的歌声很沙哑,只唱过很少的几次,低哑的歌声飘过窗棱,环绕在小小的破庙里,房梁上挂着蛛网,石像的眼睛簪着鹅黄色的小花,唇边挂着一缕浅笑,怎么也不肯睡觉的商枝逐渐觉得困了,慢慢闭上眼。
小柳枝,背净瓶
月牙梳过青丝影
萤火点灯苔作阶
镇妖邪,护山灵
幽山鬼,敲铜铃
枯藤结出红纱灯
柳枝栖在净瓶里
莫惊那,夜游行
井底星,檐角冰
旧符褪色换新绫
谁家稚子拾落蕊
簪入神像空洞睛
商枝眼眶一痛,从前不觉得,只道是寻常,现在回想起来,简直是说不清的寥落,道不明的唏嘘。
她再低头,看到石像脚下摆着两坛酒,都是上好的竹叶青,下墓之人常行于湿土之上,寒气淤积不散,老疯子让她喝酒驱寒,她总嫌这酒一股中药味,经常往里面扔冰块。
寂静的小庙里忽然响起一声轻笑,“原来是你爱喝竹叶青啊。”
商枝抿了抿唇,看着那石像,神色郑重地说道:“我听流萤提起过你们,你们很了不起,一千二百年前的事情如今又上演了,这一次,我也希望我们能赢,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些倒霉的穿书者,也为了曾经的平城,为了教我做豆腐的老板娘一家,为了三危山,为了师尊,为了我的小红……
酒坛旁边放着四个粗胚酒杯,两个已经用过,商枝拿了一个酒杯,倒了一杯酒慢慢饮下。
她知道,这就是老疯子对她的告别了。
一杯告别酒。
竹叶青本甘甜,此刻入口,只觉得极苦涩。
*
海天在极远处暧昧地交融,淡淡的雾霭织成一层轻薄如烟的纱,柔柔地悬于波涛之上。
穿着白裙的少女坐在高高的桅杆上,她栖在桅顶的姿态像一只轻盈的白鸟,羽毛化作裙摆,发丝游弋着天空上的烟霞绯色,美丽而苍白的脸庞有一种浮冰雕琢后的孤峭和寒冷,海浪在她的足尖下起落,仿佛整片海域都只是她裙裾垂落的褶皱。
她似乎在望着远处那片海,又似乎在望向更远之处。
她的目光和她美丽的容貌都让人觉得不太真实,当残阳那如血一样的光线透过她浮冰般的肌肤时,她几乎要熔化在这片灿烂又壮烈的光线里,让人觉得她和这里的海市蜃楼一样,只是光线折射出的一个美丽幻影。
巨大的白鸟从天空飞过,桅杆摇晃的阴影里,突然出现了一个雪白的影子,霜色的广袖被被风吹开,泼墨般的发丝被风吹起,极黑与极白的纠缠中,是一张揽尽了湖光山色的脸,他垂下眸,半张脸结着冰花,抬起同样覆盖着冰花的手,将江雨眠鬓边那缕被风吹起的碎发别在她的耳后。
江雨眠仰头看他,脑后的薄纱发带被风吹得飘过来,蹭着她的脸,她的声音又冷又脆,是惯常那种发号施令的,冷淡又跋扈的语气:“你站低点,不要总让我仰头看你。”
月扶疏踏着脚下的风,果然站低了些,结着白霜的长睫微微垂下,下睫毛也裹着盐粒似的霜,他漆黑的眼珠原本是高悬在雪山上的冷漠夜色,这会儿却像被人从雪山上拽进了温泉里,有温柔的水波从上面漫过去,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淡淡的温柔和温驯。
月扶疏说道:“这样够低么?”
江雨眠别过脸,留给他一个后脑勺,脑后的发带被风吹到月扶疏脸上。